
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戏曲学院院长、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、《中国戏曲志》编辑委员会委员。曾获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。多年来从事戏曲历史及理论的研究与教学,参加过多部戏曲类辞书和史书的编纂,出版过《汤显祖论稿》《中国戏曲与中国宗教》《中国戏曲文化》《昆曲与明清社会》等著作,整理出版了《古柏堂戏曲集》《消寒新咏》等戏曲文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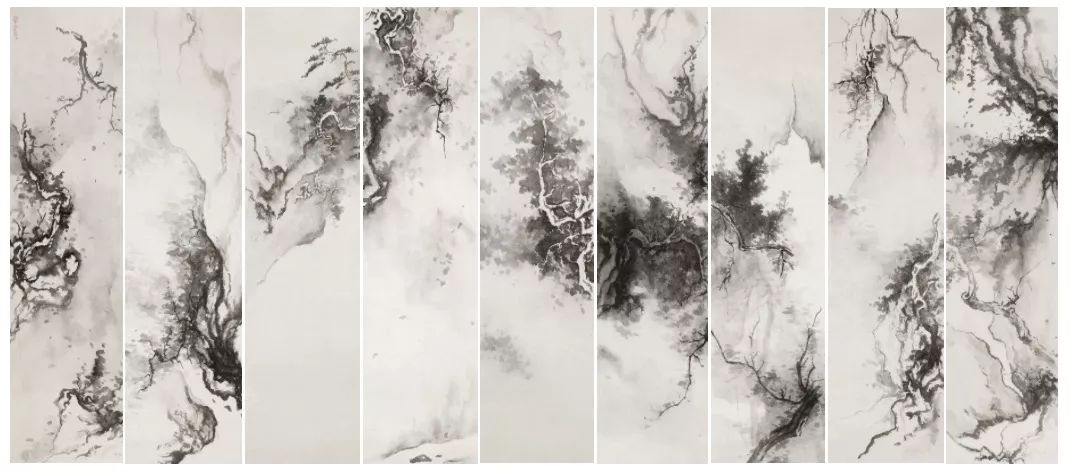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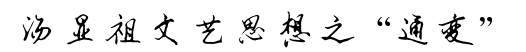 汤显祖文艺创作的杰出成就,是以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,和他的比较进步的政治思想有关,同时又受他的文艺观的具体指导。
汤显祖没有留下文艺理论的宏篇巨著。但是,在他的篇帙浩繁的诗文作品中,有不少论诗、论文、论戏、论画、论乐的言论。把它们稍加梳理,对他的文艺观即可有一大致的了解。本文试从言情、尚真、务奇、通变等几个方面,对汤显祖的文艺思想作些粗浅的探索。
“吐纳性情,通极天下之变”(《朱懋忠制义叙》),是汤显祖文艺观的又一个方面。汤显祖主张写作要学习古人的经验,要借鉴传统,但更重要的是要遵时知变,发扬自己的才情。他说:
昔人常因其“情”之卓绝而为此,固是以传。通之以“才”而润之以“学”,则其传滋甚。然以今思之,亦“时”然也。(《学馀园初集序》)
明代以八股文取士,把天下读书人训练得头脑僵化,缺少性灵,缺少独创精神。大多数读书人不仅作八股文毫无生气,即使作诗歌散文也多公式化。汤显祖慨叹:
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。能为伎巧文章,竟百十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,则乃其性少灵者与?老师云:性近而习远。今之为士者,习为试墨之文,久之,无往而非墨也。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,久之,无往而非程也。宁惟制举之文,令勉强为古文词诗歌,亦无往而非墨程也者。(《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》)
因此,他提出了“法”与“变”的关系问题。他说:
真有才者,原理以定常,适法以尽变。常不定不可以定品,变不尽不可以尽才。(《揽秀楼文选序》)
他提倡一方面要“原理”和“适法”——遵守文章的一般规矩与法度,使文章体正品高;另一方面又要尽变和尽才——充分地施展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独创性,不受“法”的绝对约束。
汤显祖又提出一个“法”与“机”的关系问题。他教导自己的儿子汤开远说:
文字,起伏离合断续而已。极其变,自熟而知之。父不能得其子也。虽然,尽于法与机耳。法若止而机若行。(《汤许二会元制义点阅题词》)
他说“法”似乎是凝固的,而“机”则是流动变化的。所谓“机”,就是“天机”,就是“人心”。他说过:“天机者,天性也。天性者,人心也。心为机本,机在于发。”(《阴符经解》)也就是说人的思想感情的活动,可以决定文章的灵动变化。在遵守似乎是不变的“法”的过程中,充分地调动自己特有的(父子所不能互代的)思想感情,是可以写出有独创性的文章的。
在写作的过程中,人的思想感情有时与文章的“法”发生矛盾。这时,汤显祖主张宁可突破法度而有所进取。他用“狂”与“狷”两种作风的不同来阐明这种主张:
子言之,吾思中行而不可得,则必狂狷者矣。语之于文,狷者精约俨厉,好正务洁,持斤捉引,不失绳墨。士则雅焉,然予所喜,乃多进取者。(《揽秀楼文选序》)
所谓“多进取者”,就是“狂”者。何谓“狂”者?李贽说:
盖狂者下视古人,高视一身,以为古人虽高,其迹往矣,何必践彼迹为也,是谓志大。以故放言高论,凡其身之所不能为,与其所不敢为者,亦率意妄言之,是谓大言。固宜其行之不掩耳。何也?其情其势自不能相掩故也。……渠见世之桎梏已甚,卑鄙可厌,益以肆其狂言。 (《焚书》卷二《与友人书》)
这种不肯践古人之旧迹,不愿守法度之桎梏的狂者,虽不象狷者那样“持斤捉引,不失绳墨”,“精约俨厉,好正务洁”,但是有大志,敢大言,富于进取心,有独创精神。在狂狷二者之间,汤显祖宁愿选择狂者。汤显祖提倡通变,实质即在于提倡进取。他欣赏肖士玮的文章,正是由于肖能“奇发颖竖,离众独绝,绳墨之外,灿然能有所言”(《肖伯玉制义题词》)有狂者的进取精神。
汤显祖自己的创作,也是实践吐纳性情,通变进取,不拘绳墨,不践往迹的主张。
他说自己“文章好惊俗,度曲自教作”(《京察后小述》)。他论戏曲的词与调的关系时,明确地提出:
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。四者到时,或有丽词俊音可用,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?如必按字模声,即有窒滞迸拽之苦,恐不能成句矣。(《答吕姜山》)
汤显祖认为不易捕捉到的丽词俊音,既是为剧中人传神写照,又是为作者吐纳性情,所以是最可宝贵的。“九宫四声”之类声律上的“绳墨”,本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,它可以由人们去认识和总结,作为写作的参考。合律依腔,是戏曲演唱实践所需要遵守的规矩。但是,声律不应成为束缚性情的桎梏。当词与调发生矛盾时,如果词的意趣神色确实可取,则不妨改调以就词。
在这一点上,汤显祖和吕玉绳、沈璟等人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差异的。吕玉绳以昆腔为“绳墨”改窜《牡丹亭》,汤显祖当然不能接受。
汤显祖提倡通变,不拘绳墨,但并不意味着忽视或否定文艺形式的重要性。他认为任何一种文章都有自己的“体”,都是按特有的形式来表现内容的。所以,他认为“貌”也是不可忽视的。他说:
言而有以传,传以久,则神明之所际也。虽然,顾可以忽貌乎哉?人之貌也,明喑刚柔,成然而具。文亦宜然。位局有所,不可以反置;脉理有隧,不可以臆属。藉其神明,有至不至。其于貌也,无不可望而知也。(《孙鹏初遂初堂集序》)
他对那些以“神明”自擅,只重意趣而忽视“体貌”的人,也是不满意的。他说:
间者文士好以神明自擅,忽其貌而不修,驰趣险仄,驱使稗杂,以是为可传。视其中,所谓反置而臆属者,尚多有之。乱而靡幅,尽而寡蕴。……(《引文同上》)
汤显祖主张写文章要精心琢磨。他《与康日颖》信中说:
读大作,攻现净浄,鲜发可喜。加以珑琢,魁卷无疑。苏有妪,卖水磨扇者。磨一月,直可两,半月者,八百钱。功力贵贱可知。吾乡文字,近不能与天下争价者,一两日水磨耳。
 汤显祖自己的戏曲创作,也绝不粗制滥造。他也是遵循戏曲文学的规律,尽可能地遵守曲律,并非“直是横行”。他曾希望王骥德帮助削正《紫箫记》不合音律之处。他也反对“拗喉披嗓”。他的《牡丹亭》大多数曲子是合乎音律的。只不过他把声律看作是可变的而已。
在汤显祖看来,作品应当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体。他把文章的要素归纳为“体、势、情、声、致”五个方面。他称赞孙鹏初的诗文:
引绳步尺,取衷厥体,勃溢者势而延豫者情;叩切者声而流莅者致。赅此五者,故幅裕而蕴深。(《孙鹏初遂初堂集序》)
在体裁、感情、意致、气势和声色的有机统一体中,“情”乃是最活跃的因素。他说张异度的文章“气质为体,既写理以入微,音采为华,复援情而极变。”(《与张异度》)决定内容与形式的变化的,还是“情”。
汤显祖是李贽为代表的“异端”思想的勇敢的实践者。他的文艺观是晚明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产物。他上承徐文长的革新勇进的作风,又与“公安派”三袁互为旗鼓,在万历文坛上是二支活跃的进步力量的代表。汤显祖是假道学的可怕的敌人,是复古主义文学逆流的强大的对手。在进步的文艺思想指导下,汤显祖的戏曲和诗文创作达到了同时代文人所达不到的水平。连一些在具体观点上和他有差异的人(例如,所谓“吴江派”的作家们),也不能不倾服于他的成就,在言情、尚真、务奇等主要方面追随他的步调。
汤显祖的文艺思想,包涵着艺术的辩证法的积极因素。但是,他毕竟是封建时代和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,在文艺观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跳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框子。例如,他的“言情”论是向封建道学的论理教条冲击的号角,但是,他根本否认“情”的阶级属性,把属于意识形态的“情”抽象化,有时甚至把它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决定性的因素,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。他重视“游道”,看到生活与创作的关系,看到生活体验的重要性。但是,他又说“诗乎,机与禅言通,趣与游道合。禅在根尘之外,游在伶党之中。”(《如兰一集序》)一旦把创作和“根尘”之外的禅机搅在一起,立即将人们引入莫名其妙的境界中去。他说“夫豫章多美才,江湖之滨,无不猥大,常然矣。”(《揽秀楼文选序》)就是说江西南昌人作文章必然高明。而王季重的浙江山阴,“大越之墟,古今冠带之国也。固已受灵气于斯。”(《王季重小题文字序》)所以王季重古文词诗歌多风人之致。这又是在宣传形而上学的地理决定论。
这类局限性,在汤显祖的文论中是显而易见的,指出来并不困难。不过,从总的方面看,汤显祖的文艺思想在他生活的当时以至后来相当长的时期,都有着广泛而积极的影响。这是应当首先肯定的。
|










